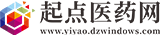杨瑞:岁时花朝——唐宋以降“花神”形象的嬗变
摘要: “花神”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流传已久。 最初的“花神”是女夷,号为“天帝之女”。 唐宋时由于道教神仙信仰的发展,修仙飞升的唐代女冠“花姑”黄令微,融合了“善种”的才能。 花信风知识与花朝节民俗的结合,使得“花神”形象开始由单一、固定的设置转向多元,表现为女夷被赋予道教仙真南岳魏夫人弟子的身份,并与“花姑”共享“花神”名号。 在花月令与明清祭祀花神的民间信仰影响下,最终形成十二月花神体系。
一、谁是“花神”?
花神信仰在民间由来已久,尤其在明清时期,每年农历二月举办的花朝节风行大江南北,花神庙亦遍布各地,广受香火供养。而关于花神的设置,在民间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规定。根据晚清吴友如《十二花神图》,一年十二月每月均有不同的月花为代表,而与之相应的则有司掌此花的花神。[1]而在俞樾《十二花神议》中,花神形象则在十二月花神基础上每月各分一男一女,阴阳协和,形成了一年十二月二十四位花神轮番主持的局面。[2]可见当时关于“花神”形象的传说和设置来源不一,大致说来是依据岁时月令排序次,而具体当值的月花和花神会随着时间流转和各地风俗有所变动,前人研究已有涉及。[3]实际上,花神在最初设立时并非由多位神仙同掌,而是单一的神职,但这一设定自唐宋时渐趋与岁时月令和民间花朝节俗相结合,从而在后世演化出十二月花神体系。这一切的源流,当从追溯花神形象开始梳理。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花神”的形象在早期文献记载中非常模糊,只是由掌管万物藩息之神兼领。《淮南子·天文训》中载,“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4]。女夷,《淮南鸿烈解》中注为“主春夏长养之神”[5],其身份尚不明确;迨至北齐隋时杜台卿《玉烛宝典》中,这位女神已经被纳入既有的神明秩序,“女夷,天帝之女,下司时,知春阳,嘉兴故鼓乐”[6]。由此可知,这位“天帝之女”的执掌是“司时”,也就是掌管月令时序以遵循节律,从而使得动植物繁衍兴旺,草木自然涵盖于其掌控范围。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古人很早就已经将草木生长与月令时序相结合。在中国古代所发明的干支纪年法中,干支相配而成的六十甲子就是记录一个生命过程的循环。[7]以此为基础,后世关于草木的重要节日和祭祀信仰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时序性,这点将在下文展开。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女夷是一位女神,号为“天帝之女”,而关于这位神的事迹却鲜少见于史籍记载,甚至被逐渐简化为一个神的名称而已[8],无从得知更多信息。但在后世溯源花神时,对这位“女夷”似乎有全新的身份和职能安排。明万历间陈懋仁《庶物异名疏》记载,“花神名女夷,乃魏夫人弟子,花姑亦花神”[9]。这里有两点变化,一是女夷由“天帝之女”一变而成为“魏夫人弟子”;二是又出现了一位花神,名为“花姑”。此说在明清时影响甚广,诸多类书中皆有所引用。[10]同时,也存在其他说法为“女夷”和“花姑”的身份作补充,同样为明万历时冯应京所撰的《月令广义·岁令一》载,“女夷,主春夏长养之神,即花神也”,又载“女夷为花神,乃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为花神”[11],意即女夷是“主春夏长养之神”,同时是魏夫人之弟子,但也有一位“花姑”成为了与女夷并称的花神。而这位“花姑”还有具体的名号,《花史左编》称,“魏夫人弟子善种花,号‘花姑’。诗‘春圃祀花姑’。按,花姑姓黄,名令徵”[12],则“花姑”姓名应为“黄令徵”。而在稍晚于此书、初刻于明天启年间的《二如亭群芳谱》中,编者王象晋甚至认为,“魏夫人弟子黄令徵善种花,号花姑,一名女夷”[13],直接将花神、花姑、黄令徵与女夷四者等同。此说显然是在前述花神传说基础上的衍生品,不足为信,但已可得见民间“花神”形象的融合趋势。综上所引,无论女夷是否为魏夫人之弟子,这位中道加入的“花姑”已经取得了与“女夷”相同的地位。那么这位“花姑”是何人?她如何与“女夷”一道成为花神,甚至取而代之?这又和“魏夫人”有何关联?有待下文进一步分析。
二、“花姑”的出现
《花木录》“花姑”条言,“魏夫人,李弟子。善种,谓之‘花姑’”[14],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提及花姑与魏夫人之关系、并且指明花姑具备“善种”之能的史料。[15]关于《花木录》一书,《类说》引《花木录》“花木疏记”条言,“唐相石泉公王方庆著《花木疏》,赞皇公李德裕著《花木录》”[16]。《旧唐书·李德裕传》载,“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筱,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及从官藩服,出将入相,三十年不复重游,而题寄歌诗,皆铭之于石。今有《花木记》《歌诗篇录》二石存焉”[17]。考上文所言李德裕著之“《花木录》”,当指代《旧唐书》本传“《花木记》”,即其所作《平泉山居草木记》一文[18],收于《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九,未涉及“花姑”内容。而《类说》所引之《花木录》,在《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与《宋史·艺文志》皆有著录,作者均题为“张宗诲”。[19]北宋名臣张齐贤第二子名宗诲,根据尹洙所撰墓志,张宗诲曾“有文集若干卷,别著《刻漏记》《花木编》二卷”[20],故推断《花木录》极有可能为其所作,约撰成于宋真宗时至仁宗庆历前。[21]遗憾的是,张宗诲《花木录》一书亡佚已久,本条记载仅见曾慥《类说》卷一三所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类说》中还有一处出现“花姑”,“《南岳夫人传》有女道士黄虚彻,年逾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夫人寓梦示之,后亦升天”[22]。那么,这两处的“花姑”指代同一人吗?
《花木录》虽已佚,但《南岳夫人传》仍有流传。南岳夫人,即东晋女冠魏华存[23],是道教上清派举足轻重的女真。据上清派早期经典《真诰》的记述,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太岁甲子,这位南岳夫人携各路仙真下降,亲传上清经典于茅山道士杨羲,杨羲作隶字写出,再传许翙、许谧。[24]南岳夫人魏华存可谓上清一脉开宗立派的祖师,也因此在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中成为地位仅次于西王母的女真。[25]她的本传,较早流传的是题为范邈所作之《南岳夫人内传》,现已亡佚,今《阳山顾氏文房小说》所存《南岳魏夫人传》实钞撮自《太平广记》卷五八《魏夫人》[26]。在该篇末尾,简要提及了“花姑”的生平:
夫人既游江南,遂于抚州并山立静室,又于临汝水西置坛宇,岁久芜梗,踪迹殆平。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迈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特加修饰,累有灵应。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亦升天。玄宗敕道士蔡伟(玮,笔者注)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768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纪其事焉。出《集仙录》及本传[27]
对比《广记》与《类说》的记载,可知“黄虚彻”与“黄令徽”为同一人,不过《广记》之记载要丰富得多。该篇末注明“出《集仙录》及本传”:所谓“本传”,应指代已亡佚之《南岳夫人内传》;而“集仙录”,则是指道教经典《墉城集仙录》。
《墉城集仙录》,原题十卷,是由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所撰的一部专门记载女仙事迹之道教史传。因撰成年代较早,版本流传情况十分复杂,现所能见到的版本主要分为明正统《道藏》六卷本和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节录本两大系统,关于这两个版本系统的关系,前人已多有比堪。[28]大致说来,《道藏》本更接近于《墉城集仙录》原本,而《云笈七签》经过宋人的加工。两本仅有两位女仙传记重出,有关“花姑”的记载极有可能源于原书已散佚的后四卷[29],现仅见于《云笈七签》节录本中。
按照《云笈七签》本中的记述,花姑,名黄灵微,自唐初以来就在江浙名山洞府间活动,“年八十而有少容”。后于武则天长寿年间前往临川郡访南岳夫人遗留之仙坛,为其修葺一新,遂于梦中得夫人指点。花姑于开元九年(721年)升化,生前身后每每有神异之象,睿宗时即为其建洞灵观,玄宗时更敕命道士蔡玮将其事迹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特召高行女冠为其仙观住持,并亲撰《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以纪其事迹。[30]该碑铭收入《颜鲁公文集》卷九,同卷《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文末同样收载女冠黄灵微事迹,两篇碑铭均题为“黄令微”[31]。罗争鸣认为,《云笈七签》本中花姑的内容当改写自这两篇碑铭[32],但笔者认为,此二篇碑铭内容当为花姑故事的底本,但是在流传过程中已经发生窜乱,迨至张君房编纂《云笈七签》时所据应为简本,故事的诸多细节已经湮没,某些信息也已发生变动。比如“华姑”变为“花姑”;女冠名讳由“黄令微”到“黄灵微”的变化;再如《华姑仙坛碑铭》中明确其为“抚州临川人”,而在《云笈七签》本中已“不知何许人也”,仅记录其“自唐初来往江浙湖岭间”;又如两篇碑铭中均记有野鹿中箭来投花姑,姑为其拔箭,然而在《云笈七签》本中“野鹿”却作“野象”。[33]诸如此类细节方面的改换还有很多,不再赘述,以上几条应足以说明《云笈七签》本并不直接改写自颜真卿碑铭,但是这些细节的改窜,到底是发生于《云笈七签》纂成时,还是在杜光庭编写《墉城集仙录》时就已成事实,无有定谳。尚存另一种可能,即玄宗时蔡玮所编写《后仙传》中记录的花姑事迹,亦有在道教经典体系中流布的线索,其中或存有不同信息。李剑国推断,颜真卿两篇碑铭内容即本于《后仙传》[34],但该书已佚,仅作一说。
虽然关于“花姑”的传说在五代宋初时就已经发生脱漏和改动,但故事的核心,唐代女道士黄令微受南岳夫人指点飞升的情节总归传承了下来。然而颇启人疑窦的是,上文所引《墉城集仙录》等史料中虽然记载“花姑”[35],也提及其为南岳夫人魏华存之弟子,然详审其行迹,并不见与草木有何特殊关系,又为何会以“善种”而知名并在后世成为“花神”呢?
三、“花神”形象的融合
关于《类说》卷一三中出现的“花姑”描述,我们暂不知晓张宗诲的依据为何,但根据上文考证能够断定的是,被称为“花姑”的女道士黄令微与“善种”没有关联。而《类说》卷一三所引《花木录》中的“花姑”却以“善种”而闻名,且这位“李弟子”与唐代女冠,无论是“黄灵微”“黄令微”“黄虚彻”等等差距都较大,即便为“女弟子”音讹,亦不能在众多记载“花姑”事迹的文本中得到佐证。所以基本能够判定,这两条“花姑”的记载应指代两个人,而非同一人。且引用本条记载的曾慥,在两宋之际就以道教学识闻名,他对于道家思想与服食养生之法甚为熟稔,曾编成《道枢》四十二卷[36],经其所筛选之记录与道教渊源深厚并不稀奇,具备一定可信度。《类说》一书的版本流传问题十分复杂,现较为通行的天启刻本存在卷次混乱、文字错讹脱衍、随意妄改等等问题,但在天启刻本与文渊阁本中皆将第一条“花姑”系自《花木录》[37],第二条注明为“《南岳夫人传》”[38],可见两者应有不同史源,也没有前后勾连的倾向。
这两位“花姑”之所以能够发生关联,乃至后世将“花姑”和“花神”移花接木到女冠黄令微身上,首要的条件即是“花”与“华”为通假字,在颜真卿两篇碑铭中记载之“华姑”,在后世流传中演变为“花姑”,从而与“善种”发生关联。另需强调的是,除了共同的“花姑”名号,她们还同出于南岳夫人魏华存门下。借由南岳夫人在道教中的影响力,再加之相关史料中留存的关于黄令微之记载更为丰富的缘故,道教女冠“花姑”的事迹渐渐流传开来。无论是神异感应还是飞升上神的显赫事迹,均使得其在民间的知名度更高,甚至出现了专门祭拜“花姑”的花姑庙[39]。而另一位同为魏夫人弟子的“花姑”,因其本身没有更多传说附会而显得默默无闻,被吸纳、转嫁于黄令微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种“融合”无论是在道教内部传承抑或是在民间信仰中都非常普遍。
吴真在检讨盛唐传奇道士叶法善从宫廷内道场道士演化为道教神祇的神化史时就指出,除了文学记载中出现了众多向壁虚造的叶法善灵异故事,还有不少其他人的事迹被移植到叶法善身上。比如景云二年(711年)正月,睿宗二女——金仙、玉真公主的入道授箓仪式,本是由另一位与唐廷渊源颇深的高道史崇玄主持,然而在道士张万福、蔡玮的笔下就变成了叶法善。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史崇玄受太平公主一力提拔而在先天政变中被一并铲除,所以教内人士在“政治正确”的选择下与史氏做出切割,而将这一殊荣转嫁于玄宗时乃至有唐一代政治地位最为崇高的道士叶法善之身。[40]“花姑”故事的复杂性虽然与叶法善层层叠加的叙述不能相提并论,但其原理是一致的。“花姑”黄令微本身因较为丰富的史料描述和玄幻的神异感应故事而在道教女真中脱颖而出,同时成为了一个“箭垛”,所有与“花姑”相关的记录、传说不断聚焦于其上,产生了一种信仰的虹吸效应。柯克兰(Russell Kirkland)认为,黄令微女仙的身份,使得其在唐宋以后女真地位下降的背景下鲜少有人关注[41],但他未曾注意到的是,作为“花姑”的黄令微已经足够幸运,还有隐藏的“花姑”在被融合后彻底消失。正是基于对“花姑”故事的层层渲染与附会,作为“花姑”的黄令微才能在后人追溯“花神”起源时,于纷纭的信仰世界中保有一席之地。
无论《类说》中有关“花姑”的记载是否指向同一人,“花姑”被后世追溯为“花神”,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即是其“善种”。关于这一点,现存史料不能提供更多细节,不过我们还可以从中古时期其他关于“花神”的描述中觅得线索。
《太平御览》引《续仙传》道士殷七七的经历中,就出现了杜鹃花神:
时或窥见三女子,红裳艳丽,共游树下。人有辄采花折枝者,必为所祟,俗传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宝惜,故繁盛异于常花。……女子来谓七七曰:“道者欲开此花邪?”七七乃问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间已逾百年,非久即归阆苑去,今与道者共开之。”[42]
这里杜鹃花神的形象异常模糊,不知其姓名、身份,但知其能保护花木,惩罚折花者,同时能够随心所欲地掌控杜鹃花的开落,使其“繁盛异于常花”。再如《酉阳杂俎》中所记三位化身为女子的草木,为报答崔处士护佑抵挡风神摧折,而献可使其长生之桃李花的故事。[43]可见在唐宋时期与花神相关的偶发故事中也存在一些共同点:花神具备人的情感与行为,一般为女性;能够护佑草木;掌握草木的繁衍生息,由此也奠定了此后民间信仰中关于“花神”形象的基本面。
四、“二十四番花信风”与花朝节
唐宋时期之所以是“花神”信仰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一个突出原因即是“花神”形象的多元化肇基于此,具体表现为,“女夷”之外又生出“花姑”,“女夷”亦始被纳入道家神仙体系而成为“魏夫人之弟子”。但是此时的“花神”形象多为固定的、一脉相承的,还远未形成明清时系统而富有节令气息的十二月花神,那么单一类型的花神是如何向十二月花神体系转变的呢?
上文在介绍最初的“花神”——女夷时就已交代,草木的荣枯与时令密不可分,而女夷正是“司时”的天神,掌控了时间,就意味着掌控了草木存亡之根本。 人们根据最朴素的生活经验,将与草木生长相关的重要节点与岁时顺序相结合,从而在唐宋时形成了“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
程杰考证认为,现在流行的花信风之说出自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观点有误,实际上此说应来自南唐徐锴的《岁时广记》;因两书在文献中均被称作“《岁时记》”,又值后书早佚之故,才发生了误属。[44]笔者认为这一说法较为可信,且徐锴《岁时广记》一书虽佚,在南宋程大昌《演繁录》中尚存引其“花信风”的记载。“三月花开时风,名花信风。初而泛观,则似谓此风来报花之消息耳。按《吕氏春秋》曰:‘春之德风,风不信,则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风者,风应花期,其来有信也。徐锴《岁时记·春日》”。[45]由此可知,至晚在唐末五代时就已经出现了花信风的说法,但此时的“花信风”还是专指春三月花开时的风信,虽已经初步衍生出风信与花期的对应关系,但与后世“二十四番花信风”尚相去较远。“花信风”理论承续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还是在宋代。
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首见于北宋晏殊诗句,“春寒欲尽复未尽 ,二十四番花信风”[46],惜仅存散句而未见其解。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东皋杂录》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最后”[47];宋季陈元靓《岁时广记》“花信风”条补充,“五日一番风侯”[48]。那么二十四番花信风即百二十天左右,近四个月时间,较之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初春、初夏时段明显偏长。实际上,宋人所谓“自初春至初夏”,应是从小寒至谷雨的这一时段,五日共六十时辰为一侯,三侯为一气,小寒到谷雨正经历八气二十四侯,对应二十四番花信风[49]。古人关于春的计算,是自冬至始,正所谓“冬至一阳生”,而为何花信风当自冬至之后的第一个节气小寒开始?明人王逵有这样一番见解:“三建虽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然却但以冬至为一建,小寒为二建,大寒为三建也。何以知其然也?盖造历始于冬至,察天气也;候花信之风始于小寒,察地气也;辩人身之气始于大寒,以厥阴为首,察人气也”[50]。这是据《周易》象数理论所作之解释,小寒是干支历法中丑月之始,故而符合古人地气滋发、春阳渐生之认识。[51]虽然二十四番花信风的理论在宋代只是初具萌芽,且仅覆盖初春至初夏约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段。但应无疑问的是,花信与物候、节气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每一物候也渐次产生其最具代表性的花品,距扩展为全年十二月均有代表之月花仅有一步之遥了。
在南宋时形成“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并不是偶然,因为几乎与此同时,以春日赏花为旨趣的花朝节也正式设立起来。吴自牧所撰《梦粱录》中,就记录了南宋临安城花朝节的胜景:“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此日帅守、县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以农桑,吿谕勤劬,奉行虔恪。天庆观递年设老君诞会,燃万盏华灯,供圣修斋,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来无数。崇新门外长明寺及诸教院僧尼,建佛涅槃胜会。罗列幡幢,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竟日不绝。” [52]在这一天,临安城游人如织,官家、佛道人士以及平民,各种欢庆活动纷至沓来。吴氏明确指出,“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53],此时正值春花盛放,赏花士庶络绎不绝,“二十四番花信风”对于游人而言可谓是一份全面的“赏花时间指南”。花信风和花朝节的出现,正是促使单一类型花神形象结合岁时月令而转向十二月花神形象的重要契机。
实际上,早在南宋末年花朝节形成定俗之前,二月中旬踏青赏花已经在民间广受追捧。[54]魏晋南北朝以降,“花朝”一词就出现在众多诗赋中[55],“花朝月夕”既可指代良辰美景,有时也用于代表二月半以及与之相对的八月半(中秋)[56]。在这些美好的时刻,一系列赏玩、庆祝活动应时而出,在两宋之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民众庆祝花朝、出游探春的盛况。[57]其“于是相继清明节矣”一句也说明,虽然北宋开封城还未出现正式的“花朝节”,但是庆“花朝”的活动已经深入人心,业已被视为清明之前的又一重要节俗。可以说,岁时月令与花朝节俗以及花信风的结合,反映了这一时期草木知识体系在民间信仰、社会生活中的演变流传。
五、岁时月令对“花神”形象的再塑造
“二十四番花信风”集中于一年中花卉的盛放期,主要是春夏时节,而其发展为覆盖全年的花月令,始于唐宋,最终至明代才得以完成。“月令”,即岁时节令,包含朝廷随季节所制定的政令,亦包含民俗节日的内容。而“花月令”,即以花卉为中心,记录了它们在一年中按月份的盛放与凋零,是月令逐渐世俗化、实用化的衍生内容。[58]在明人程羽文所撰《花历》中,因其感到“花有开落凉燠不可无历”[59],遂对花之开落按照月令顺序进行排次,形成了一部“花月令”。如果我们将王逵对于“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解释与程羽文《花历》以及吴友如“十二月花神”对比来看(表1):
表1 “二十四番花信风”、《花历》以及“十二月花神”内容对照表
可以看出,虽然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的节气与农历月份并不能按月对应,但是在同一时段中对于代表花的选择方面,花信风、花月令乃至最后形成的十二月花神,具备相当的一致性。尤其《花历》的十一月,明确写道“花信风至”[62],可见“花历”“花月令”的制作与花信风息息相关,后者参考了前者的排布。不仅如此,《花历》的思路与花信风高度相似。在花信风缺失的农历五、六、七、八、九、十月份,《花历》选取的依然是当月草木开落的代表和突出时令的现象,借此完成了花信风未能覆盖的时间版图,从而形成了草木与一年月令相始终的循环。
虽然不能说花月令一定是在花信风的基础上生成的,但它们无疑是民间认知中将草木与物候、月令知识结合的产物,两者的理念不相扞格,而是交相用、曲相成。只有形成了此类时令性循环,十二月花神说才具备成立的条件。上文我们说到,唐宋时期的“花神”一般为女性,能够护佑草木繁衍生息。而在十二月花神的体系中,“花神”已经不再局限于女性,亦不强调其是否有“善种”等能力,而是尽量选取与月花相关的名人轶事、历史典故,以将花神的影响力最大化,这在吴友如的十二月花神版本中已经有所体现。而在俞樾更为详细的《十二月花神议》中,细绎为“议之上”与“议之下”两部分,将各月花神男、女对举,并详列出其成为花神之理由,其排布如下(表2):
表2 俞樾《十二月花神议》花神排布表
俞樾认为世俗所传之十二月花神“鄙俚不经”,遂对十二月花神加以勘定,俞氏列举之理由不再赘述。[63]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俞樾在十二月花神之外,又增加一佛一道两位“总领群花之神”,一位是迦叶尊者,因其于灵山百万众前拈花一笑;而另一位女神,则是“魏夫人”,因其为女仙之最贵者。也只有在此处,我们才能看到十二月花神体系中对唐宋时“女夷”“花姑”等花神因素的一点保留,“魏夫人”在这一体系中取代了名气稍逊于她的两位弟子,最终成为民间信仰中十二月花神之首。
十二月花神的出现以及修订,并不能简单视为文人闲来无事的爱好。与唐宋时“二十四番花信风”与花朝节相伴相生的现象非常类似,此十二月花神的出现也与民间祭祀花神的民俗相呼应。明清时期,花朝节的日期随着各地习俗和自然气候的不同可能安排在农历二月初二、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但节日这天往往被视为“花神”的生日,从而在赏花、游玩等传统习俗外,还有在花神庙进行祭祀的活动。明代林世远、王鏊等纂(正德)《姑苏志》中,就收录了南宋时苏州民间祭献“百花大王”的热闹场面,“宋韩子师彦古镇平江,夜闻鼓笛喧訇。问:‘何处作乐?’老兵言:‘后园百花大王生日,府民年例就庙献送’”[64]。至明清之际,已明确出现祭花神时主祀、陪祀的传统,“阁中置木主以奉祀百花之神,如东皇封姨亦与焉。两傍配以历代之才子美人,如司马长卿、卓文君、秦嘉、徐淑之属。每岁时及花朝诞辰,命美人设果礼致祭,或歌新诗以侑之”[65]。迨至清代,随着十二月花神说的成熟与广泛传播,各地花神庙中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十二月花神布局。《书隐丛说》就记录了雍正朝浙江总督李卫在西湖岸上建造花神庙的故事,“中为湖山土地,两庑塑十二花神,以象十二月。阳月为男,阴月为女,手执花朵,各随其月,其像坐立欹望不一,状貌如生焉”[66]。在花朝节当天,祭祀花神俨然成为节日的代表性内容,“虎丘花农争于花神庙陈牲献乐,以祝神厘,谓之花朝”[67]。虽然受地方因素的影响[68],但主花神搭配十二月花神的总体框架还是被保留下来。流传至今,祭祀花神在汉族节俗中渐趋式微,只有在今北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尚有花神庙的地名或景观遗存,而在彝族等少数民族群体祭祀活动中,仍可得见较为完整的“祭花神(索玛花)”仪式[69]。
民众视花朝节为“百花生日”,亦是祭祀“花神”之日,该祭祀哪位花神抑或哪几位花神就是实实在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吴友如、俞樾等等众多的版本,以迎合或者补完民间需求。可见,花信风与花朝节、十二月花神与花朝祭花神的互动,促成了草木知识与民俗相辅相成的合作,在这一过程中,“花神”形象因与岁时月令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从唐宋时单一类型的花神向十二月花神的转变。
六、小 结
本文从唐宋时期的“花神”信仰出发,分四个阶段探讨了“花神”形象的递嬗过程:第一阶段,“花神”为“天帝之女”女夷;第二阶段,由于中古道教神仙信仰的发展,修仙飞升的唐代女冠“花姑”黄令微,融合了“善种”的才能;第三阶段,在花信风、花月令等草木知识,以及民间花朝节祭祀花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明代“花神”形象由单一类型的女神信仰转向多元,表现为女夷被赋予道教仙真南岳魏夫人弟子的身份,与“花姑”共享“花神”头衔;第四阶段,明清民间形成普遍的十二月花神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花神”身份的转变成为道教信仰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而有关草木的知识如花信风、花月令等又与花朝节庆、祭祀等民间信仰活动互为表里,最终酝酿出十二月花神体系。“花神”形象逐渐由单一、与草木息息相关的女神形象,向多元、注重传播与影响力的世俗人物形象转变。这既是知识、信仰与民俗交织的结果,也反映了不同宗教因素在信仰世界的激烈争夺,使人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神界实际上是世俗权威的一种拟象”[70]。随着民间信仰和市民生活的繁盛,有关“花神”的传说最终成为丰富民众生活的一种资源,不再具有信仰方面的绝对权威与纯粹。
注 释
[1] 参见(清)吴友如:《吴友如画宝》“古今人物图 第一集下”,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4页。
[2] 参见(清)俞樾:《曲园杂纂》卷四四《十二月花神议》,《俞樾全集》第9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68—578页。
[3]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原始宗教对草木信仰、意涵、文学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具体关照到不同种类的“草木”如桃、柳、桑等研究诸层面。相关研究可参见:〔日〕水上靜夫:《中国古代の植物学の研究》,東京:角川書店1977年版;〔日〕水上靜夫:《花は紅・柳は緑:植物と中国文化1》,京都:八坂書房1983年版。对于花神形象的演变,前人研究多以明清时期为主,对花神起源和形变着墨较少,尚存有讨论空间。参见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6页;于丹:《花神形象的流变——兼探清代小说中的花神意蕴》,《学术交流》2007年第7期;高雅:《花朝节及十二花神的传说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4] (汉)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32页。
[5] (汉)刘安:《淮南鸿烈解》卷三《天文训》,《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页。
[6] (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二,《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页。
[7] 参见刘晓峰:《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7—50页。
[8] 在唐代《初学记》《岁华纪丽》等书中,将“女夷”解释为“神名也”。参见(唐)徐坚:《初学记》卷三《岁时部·春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页;(唐)韩鄂撰,(明)沈世龙、(明)胡震亨同校,窦永怀点校:《岁华纪丽》卷一《春》,《中华礼藏·礼俗卷·岁时之属》第1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7页。
[9] (明)陈懋仁撰:《庶物异名疏》卷三〇《鬼神部·女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1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250页下。
[10] 如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清代厉荃《事物异名录》“神鬼部”皆沿用此说。参见(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七〇《花类·总》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下;(清)厉荃原辑,(清)关槐增纂,吴潇恒、张春龙点校:《事物异名录》卷二八《神鬼部·花神》,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387页。
[11] (明)冯应京辑,戴任增释:《月令广义》卷一《岁令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72页下、573页上。
[12] (明)王路纂修,李斌校点:《花史左编》卷一七《花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58页。
[13] (明)王象晋辑:《二如亭群芳谱》贞部卷一《花谱简首·花神》,复旦大学古籍部藏清康熙初年沙村草堂本,第4页a。关于《二如亭群芳谱》的版本研究,详可参见崔建英:《<二如亭群芳谱>版本识略》,《文献》1986年第2期。
[14] (宋)曾慥辑:《类说》卷一三《花木录》“花姑”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第6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影印明天启六年岳钟秀刻本,第239页上。关于《类说》一书版本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李更:《李盛铎旧藏<类说>“七十卷本”残卷探析——兼议明天启刻本面貌的形成》,《版本目录学研究》第8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230页;关静:《<类说>天启刻本系统学术价值再探》,《文献》2020年第6期。文中所引《类说》为天启刻本,又引以天启刻本早印本为底本的文渊阁本加以参照,属六十卷本系统。限于疫情之故,暂无法对五十卷本系统进行检视,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补充讨论。
[15] 参见杨宝霖:《宋人张宗敏<花木录>未全佚》,《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第63页。“张宗敏”为“张宗诲”之讹。
[16] (宋)曾慥辑:《类说》卷一三《花木录》“花木疏记”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第62册,第238页下。
[17]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28页。
[18] 参见(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下《别集卷第九》,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684—685页。
[19] 参见(宋)王尧臣等撰,(清)钱东垣等辑释:《崇文总目》卷三《小说类下》,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粤雅堂丛书》本,第97页下;(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四·史类第五·食货》,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93页;(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四·子类·农家类》,卷二〇六《艺文五·子类·小说类》,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05、5226页。
[20]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七《故紫金光禄大夫秘书监致仕上柱国清河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张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5页a。
[21] 关于张宗诲为何会撰《花木编(录)》之类的书籍,与他的生活环境关联甚密,最重要的原因是其父张齐贤得到了唐代宰相裴度的别墅——午桥庄。午桥庄早在裴度时就以自然景致而闻名,号称“花木万株”,入张氏手时仍“有池榭松竹之盛”,故张宗诲具备观察花木十分便利的条件。参见《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第4432页;《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第9158页。
[22] (宋)曾慥辑:《类说》卷六〇《拾遗类总·花姑》,《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第62册,第1022页下。原书阙“升天”二字,据文渊阁本补。(宋)曾慥编:《类说》卷六〇《拾遗类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47页上。
[23] 参见周冶:《南岳夫人魏华存新考》,《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
[24] 参见〔日〕吉川忠夫、〔日〕麦谷邦夫编,朱越利译:《真诰校注》卷一九《翼真检第一·真经始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2—573页。
[25] 参见(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5页。
[26] 参见佚名:《南岳魏夫人传》,(明)顾元庆编:《阳山顾氏文房小说》,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第8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明正德嘉庆间顾元庆刻本,第223页上—226页下。关于《南岳夫人传》的史源情况,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14页;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474—1475页;武丽霞、罗宁:《<南岳夫人内传>考》,《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
[27]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五八《女仙三•魏夫人》,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61页。
[28] 相关研究可参见:李丰楙:《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09—114页;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第五卷,第1457—1474页;罗争鸣:《杜光庭道教小说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01—115页。
[29] 参见樊盺:《<墉城集仙录>版本考论》,《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324页。
[30] 参见(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一一五《花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50—2552页。罗争鸣《墉城集仙录辑校》卷七、卷八据《云笈七签》卷一一五、一一六补,见(唐)杜光庭撰,罗争鸣辑校:《墉城集仙录》卷七《花姑》,《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79—681页。
[31] (唐)颜真卿著,(清)黄本骥编订,凌家民点校、简注、重订:《颜真卿集》第一部分《文·碑铭》,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7页。
[32] 参见(唐)杜光庭撰,罗争鸣辑校:《墉城集仙录》卷七《花姑》考订,《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第681页。
[33] 参见(唐)颜真卿著,(清)黄本骥编订,凌家民点校、简注、重订:《颜真卿集》第一部分《文·碑铭》,第116—117页;(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一一五《花姑》,第2550—2551页。薛爱华(Edward Schafer)也关注到黄令微文本中“野象”和“野鹿”的区别,参见Edward Schafe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hrine of Wei Hua-ts’un at Lin-ch’uan in the Eighth Century”,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15, 1977, p.136.
[34] 参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第一卷,第204页。
[35] 唐代女冠黄令微访道成仙之事,又见《五色线》卷下节引作“董灵微”,但并未注明出处为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引作“黄灵微”,考其史源应为《云笈七签》,两处均指代“黄令微”。参见(宋)佚名撰,唐玲整理:《五色线》卷下《花姑》,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八编 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483页;(元)赵道一:《仙鉴》后集卷四《花姑》,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2220—2225页。
[36] 关于曾慥《道枢》的研究,可参见〔日〕宮沢正順:《曾慥の書誌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版;黄永锋:《<道枢>成书及其流传三题》,《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
[37] 参见(宋)曾慥编:《类说》卷一三《花木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3册,第236页下。
[38] (宋)曾慥编:《类说》卷六〇《拾遗类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3册,第1047页上。
[39] 参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江南西道一·宣州·宣城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48页。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此时的花姑庙与明清时的花神庙不同,仅仅是对花姑黄令微本人的信仰崇拜。
[40] 参见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7、49—50页。
[41] 参见Russell Kirkland, “Huang Ling-Wei: A Taoist Priestess in T"ang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 Vol. 19. 1991, pp. 47-73.
[42]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五二《神仙五二·殷天祥》,第321页。
[43] 参见(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续集卷三《支诺皋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13—1615页。
[44] 参见程杰:《“二十四番花信”考》,《阅江学刊》2010年第1期。另有研究认为二十四番花信风出自《荆楚岁时记》,实际上缺乏文献考证。
[45] (宋)程大昌撰,许逸民校证:《演繁录校证》卷一《花信风》,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4页。
[46] (宋)晏殊、(宋)晏几道撰,黄建荣、戴训超整理:《临川二晏集·晏殊集·补遗·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47]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七《唐人杂记下》,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22页。
[48] (宋)陈元靓撰,许逸民点校:《岁时广记》卷一《春·花信风》,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5页。
[49] 关于二十四节气的生成与意义,可参见刘晓峰:《二十四节气的生成结构》,《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
[50] (明)王逵:《蠡海集》“气候类”,《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
[51] 明清时,二十四番花信风自小寒开始已经形成共识。参见(清)袁景澜撰,甘兰经、吴琴校点:《吴郡岁华纪丽》卷二《二月·花信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52] (宋)吴自牧撰,阚海娟校注:《梦粱录新校注》卷一《二月望》,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16—17页。
[53] (宋)吴自牧撰,阚海娟校注:《梦粱录新校注》卷一《二月望》,第16页。
[54] 对于花朝节的溯源与介绍,相关研究可参见:〔日〕中村喬:《中国歲時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1993年版,第194—210頁;常建华:《岁时节日里的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7—82页;〔日〕中村裕一:《中国古代の年中行事》,第一冊 春,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380—384頁;李菁博、许兴、程炜:《花神文化与花朝节传统的兴衰》,《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马智慧:《花朝节历史变迁与民俗研究——以江浙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学刊》2015年第3期。
[55] 对于花朝节诗文的梳理,可参见凌帆:《花朝节文学与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56] 《西湖游览志余》中有对“花朝月夕”的总结性陈说,“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盖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两月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为花朝,八月半为月夕也”。参见(明)田汝成辑撰,刘雄、尹晓宁点校:《西湖游览志余》卷二〇《熙朝乐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38页。
[57]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12—613页。
[58] 关于月令性质、内容的变化,可参见余欣、周金泰:《从王化到民时:汉唐间敦煌地区的皇家<月令>与本土时令》,《史林》2014年第4期。
[59] (明)程羽文撰:《花历》,(清)陈梦雷、蒋廷锡等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卷一一《花部汇考二》第531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1940年版,第51页a第一栏。
[60] 参见(明)王逵:《蠡海集》“气候类”,《丛书集成初编》,第34—35页。
[61] 参见(清)吴友如:《吴友如画宝》“古今人物图 第一集下”,第39—44页。
[62] (明)程羽文撰:《花历》,(清)陈梦雷、蒋廷锡等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卷一一《花部汇考二》,第51页a第三栏。
[63] 参见(清)俞樾:《曲园杂纂》卷四四《十二月花神议》,《俞樾全集》,第568—578页。对于十二月花神与月令相对应的具体解释,可参见殷登国:《中国的花神与节气》,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62页。
[64] (明)林世远修,(明)王鏊等纂:(正德)《姑苏志》卷五九《纪异》,《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苏州府部》第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第300页下。《夷坚志补》中收录了此条材料,但未注明出处及收录原因,参见(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补》卷一五《百花大王》,《夷坚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5—1686页。
[65] (清)黄周星撰,谢孝明校点:《九烟先生集》卷二《将就园记·将园十胜》,《黄周星集 王岱集》,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8页。
[66] (清)袁栋:《书隐丛说》卷一四《花神庙》,《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0页上。
[67] (清)袁景澜撰,甘兰经、吴琴校点:《吴郡岁华纪丽》卷二《二月·百花生日》,第65页。此条完整内容是对江南花朝节俗的总括。
[68] 比如苏州在明洪武中所建桐桥花神浜花神庙,祭祀的花神姓李,冥封永南王,旁列十二花神。同样是在苏州,清代所建虎丘试剑石左花神庙,祭祀的则是乾隆时花农陈维秀,因其窖薰之法解决了乾隆南巡时檄取“唐花”的燃眉之急,为当地花农带来实利。参见(清)顾禄撰,来新夏、王稼句点校:《桐桥倚棹录》卷三《花神庙》,《清嘉录 桐桥倚棹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71—272页。
[69] 参见高翔:《黔西北彝族“祭花神”仪式的宗教内涵与象征意义》,《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
[70] 〔美〕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著,廖涵缤译:《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72页。
原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9卷,转自 宋史研究资讯公众号。